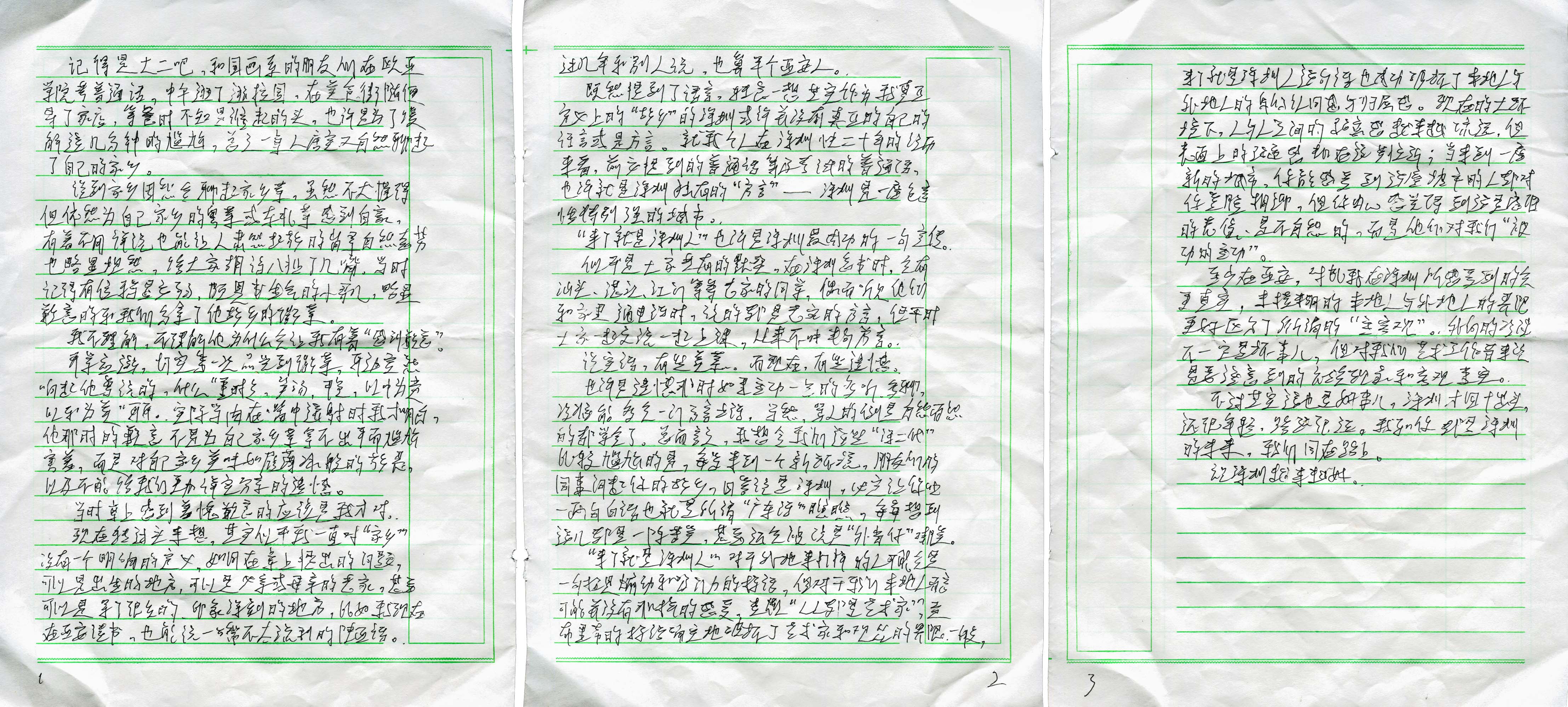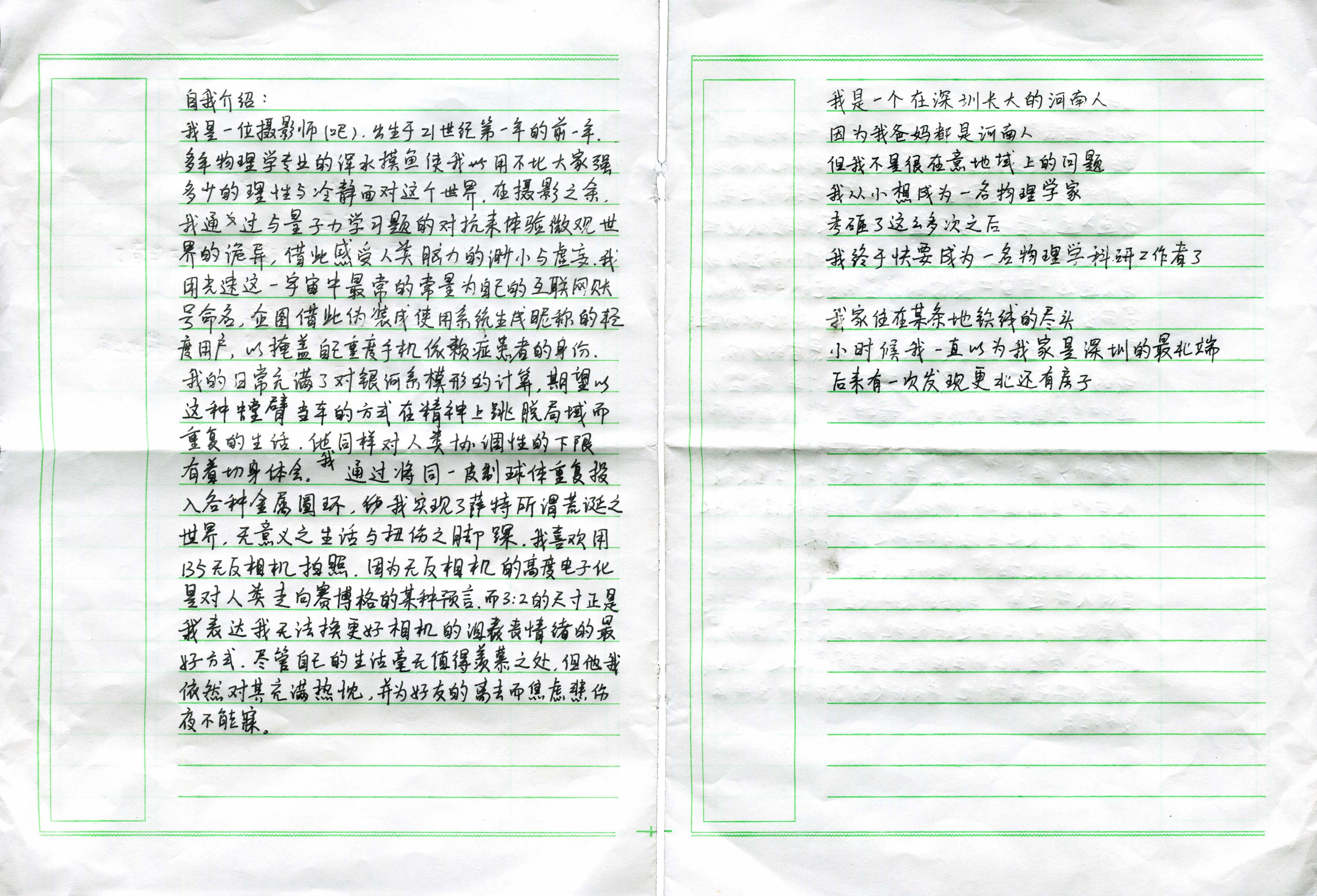我从小时候的一张报纸开始回溯自己对于深圳的地域认知,在项目开始时,我无法将故乡这一概念投射在这座新兴的移民城市。同时,我也没有把这座城市作为一个可以寄托的精神对象,在我的身份认同中,家乡是一个模糊且暧昧不清的地点,它可以是父亲或者母亲的出生地,甚至可以是我正在上大学的城市
2020年初疫情爆发,我被迫滞留在这座城市一段时间。我开始思考自己与这座城市的关系,这里是我身体上的故乡,但在精神上,这里并没有完全扮演着一个“故乡”的角色。带着这些问题我开始探寻这个城市,沿着前人所留下来的口述,老照片,文献,等私人化的线索,我拍摄了一些关于深圳的景观,并走访了同样对身份认同缺失的同龄人,在对这座城市中提出问题与用影像去探寻这座城市的过程中,我慢慢找到了自己缺失的身份认同。
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,我一直是模糊的,我出生在这座城市,但是在过 年的时候总会离开这座城市回老家,老家的人总是说着一些我听不懂的方言。可是我又无法将这座城市当作自己的精神故乡,他没有丰富的文化底蕴, 也没有自己的方言。如果这里是家乡,那每年过年回去的遥远村庄是什么地方呢?我带着这些问题开始去着手做一些对于深圳的研究,我先去拜访了一些 早些时候来到深圳的移民,他们都来自深圳的北方,有些来自江南,有些则来自东北。我从他们手上收集了很多关于深圳早期的照片和文献,也听到了很多关 于这座城市的历史,内容从政府政策到民间传说,再到灵异故事。
这些老照片不仅是单纯的图像,更是一种物件,有着被使用,被保存, 被观看的痕迹,这些有温度的图像将我带到了我出生之前的时空。照片中的人所携带的身份信息被我刻意抹去,制作了一种似乎在发光的效果。我希望观看者可以不被人物的表情或长相所吸引,更多的关注于照片的 时代背景和“被拍摄者所处在某一场域”这件事本身。
带着这些收集到的线索,我开始游走在深圳的街头,在这个城市中,如 果你一直向南行走,会遇见一道有形的边界线,这道边界线从郊区延伸 到市区,再延伸到郊区。沿着边境线开始进行拍摄时,发现了很多来自意识形态的冲突,比如繁 体字与简体字的使用,建筑风格的改变,以及边境产业的出现。例如往返于深港两地的的士司机,他们通常拥有两套牌照,一套黑色一 套蓝色,但这些冲突在我们的意识形态中又被默许了。
我沿着边界线行走时,我被告知深圳曾经有“二线关”的存在,一线 关是深圳和香港的边界,而二线关是深圳最初设立时和周边地区隔离开 的一个实体边界,与一线关相同,有着绵延的铁丝网和岗亭,并设立了 12 个边检站,出入人员都要拿着身份证明。这些边检站在我出生后就慢慢被弃用了,以前的巡逻公路变成了绿道, 岗亭变成了乘凉用的凉亭,边检站变成了公交站。这条边界线已经消失了, 但是留下的景观提醒着我,这里曾经存在着一条有形的边界。
在城市中行走的同时,继续寻找着深圳的“根”,我拜访了许多和我有 关系的长辈,试图去寻找我为何存在于此的原因。他们都很乐意谈起早期深圳的经历,但是说着说着总会兴奋的提到自己 的家乡,就算在深圳生活了几十年,他们的“乡愁”总是属于远方。
而我的“乡愁”呢?
与此同时,我拜访了一些和我一样出生于深圳的同龄人,和他们分享了 共同的困惑,并让他们写了一些关于自身身份认同的自述。其中有人认为深圳不是自己的家乡,有人认为自己有着两个家乡,深圳 只是其中的一个。在搜集老照片的过程中,“世界之窗”这个景点频繁的出现各家各户的 相册中,在深圳刚开始发展的时候,市内的大型娱乐景点只有世界之窗, 那是一个有着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名胜古迹的公园,虽然只是微缩尺寸, 但是并不影响人们和它们合照的热情。
我尝试去了解他们关于深圳的故事以及所生活的地区,并选了代表性的 地点为他们拍了一些环境肖像。在搜集老照片的过程中,“世界之窗”这个景点频繁的出现各家各户的 相册中,在深圳刚开始发展的时候,市内的大型娱乐景点只有世界之窗, 那是一个有着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名胜古迹的公园,虽然只是微缩尺寸, 但是并不影响人们和它们合照的热情。我顺着收集的照片,再次来到了这个深圳早期仅有的娱乐景点,我行走 在其中,仿佛这些地点仍保留着那些上个世纪的残影。
我尝试用摄影这个媒介去解决我所困惑的问题,摄影是不会骗人的,同时也是最会骗人的。我只能通过老照片和文献去认识那个遥远的过去的时代,并在现在的时 空中寻找那些稀疏的线索。在项目的不断推进中,我了解到了关于深圳的过去,现在,以及未来, 归属感所带来的身份认同逐渐形成,我慢慢找到了自己所缺失的那一部分“乡愁”。